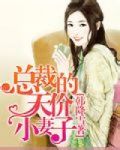真正的人生,是从懂事开始的,即知道自己的生存状况和应该承担的责任。一般是从了解父母和家庭情况开始的。我的懂事是从那次回家要学费开始的。
那是小学三年级开学一个月后,那天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北边桥山最高峰上空,一片白云,在蓝蓝的天空映衬下,变幻着各种形状。一行大雁排着“一”字形向南飞过,不时传来“嘎———嘎”的叫声。
“你还不服气?再摔一次嘛!”我不停地自言自语,不停地奔跑着。
看到秋庄稼收获后而麦子还没种下的田野里光秃秃一片,就朝着家里的方向从地里斜插过去。刚才教室里那尴尬的一幕不断浮现……
“没有交学费的同学,请站起来!”班主任苏老师在午饭后自习一进教室就说。像母亲一样可亲可爱、给我们当了两年班主任、教语文的赵老师暑假调走了,由新调来的一个叫苏中林的英俊而严厉的男老师接任。
全班五十多名学生,竟然只有我一个人站了起来。“李厚品,我都催促三次了,全班就剩你一个了。你现在回家拿钱去!”这时同学们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一下子从脸热到耳根、脖子,倔犟地用余光扫视了教室,无奈地夺门而出,身后传来个别同学的嘲笑声,特别是王建设的笑声最刺耳。
自从两年前进校门,我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就是陆续与班上的男同学摔跤都取胜了。我以为征服了班上的男生,全班就是我的地盘了。
可这学期班上来了两个留级生,一个李满堂经过两次摔跤已经服了,而王建设只被我摔倒一次,他还不服呢。“咱再来嘛,张狂啥哩?”想着跑着,二三里路不知不觉就到家了———红苕窑的第二排村子。
我们队是第五生产队,是窑堡公社窑堡大队红苕窑上五个生产队之一。窑堡大队由五个窑居生产队和五个堡子房居生产队组成。红苕窑散布在由桥山向关中平原过渡的坡台式地段上。这些住户不像堡子那样密集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选择较高的埝头便于挖掘窑洞,也可能是一户一户陆陆续续从各地逃荒迁来的,反正它像天女散花一般稀稀拉拉占了半个窑堡生产大队的摊场。此处的土地干旱而贫瘠,只适宜栽种红苕这种食物。正因为旱地含沙土壤长出的红苕甘甜面腻如板栗一样,它不仅救下这些逃荒人的性命,而且生熟红苕拿到街道很受顾客青睐,成为这些逃荒人置办家当和衣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主要资金来源。
这些逃荒人也像红苕对水肥要求不高一样,他们对生活也没有过高的奢望,只要有一个遮风挡雨的窑洞,哪怕每天只有红苕这样的食物充饥就相当满意、乐意在此落脚。可能是这个缘由,堡子人把这一大片窑居的村落叫做红苕窑。农业合作社以后,窑堡大队由北向南把红苕窑分了一、二、三、四、五五个生产队,和房居堡子的六至十生产队,平分了窑堡大队的半壁江山。
我们队在红苕窑的南端,由南往北依次沿四个埝头分散居住,其中最南端和最北端的埝头各住了三家人,靠近中间的两个埝头居住了生产队的大多数人。可能是为了生产方便,分了南窑上和北窑上两个组。北窑上也叫李家窑,是因为清朝光绪年间灾荒后我们李家的先人最早来到这个地方开荒种地居住。我家在北窑的中间偏西一点。
父亲还在家,我一边擦汗一边给父亲说老师要学费的事儿。“给老师说说,再缓缓。”父亲听了,无奈地说。
“只有五毛钱啊……”我说。
“看你这娃说得轻巧!咱家连一分钱也没有,还只有五毛钱?你二哥吃饭时也要,还是没有。你给老师好好说说,再缓缓吧。”说完父亲拿了锨,对东窑里说了句“你们妇女拾棉花哩,你也该走了”就出了院子,可能是上工去了。我们家有两面相互垂直的窑洞,朝北的正窑和朝东的偏窑窑门口紧紧挨在一起。听父亲说是先人在清朝光绪年间打的。
想起家里放钱的地方———北窑半墙上一个腰窝,我赶快拿了小方桌,站上去,踮起脚尖,在腰窝里找寻了半天,一分钱也没找到。
“好娃哩,你大咋能哄你哩?家里实在没钱啊。你二姐就因没钱这一学期都没去书坊(学校)了,回队里跟你大哥、大姐出工了。你要好好上学,不要分心,去给老师好好说一说。”妈妈在东窑的灶房里洗完碗筷,一边擦手,一边说。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本站只支持手机浏览器访问,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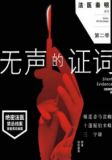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无限流]](/bookcover/123/123801/123801s.jpg)